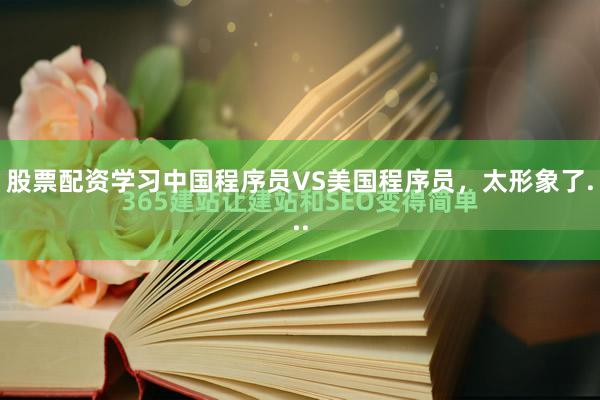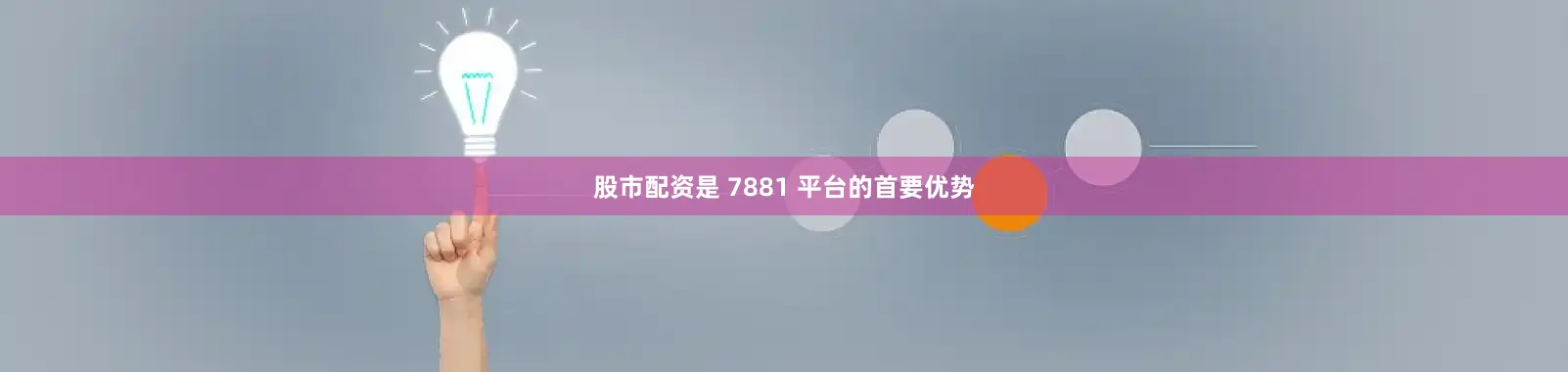“1984年7月12日清晨,’广州来的钟教授到了吗?’值班的老专家推开会诊室,声音低得只能贴耳。”那一刻,北医三院的走廊里气压极低,空气里满是急救药味。病房另一头,87岁的叶剑英元帅高烧不退、呼吸沉重,监护仪闪烁的红灯像战场上紧迫的信号弹。
病情兜兜转转几周,肺部感染屡控屡发。负责保健的医护组将所有能想到的抗生素、激素轮番使用,收效却寥寥。眼见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,院方不得不连夜拟好病危通知书。与此同时,几个机关动作迅速:人民大会堂照例走流程,布置悼念会场;中央礼宾司草拟告知各国驻华使团的电文;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接到的指令是“随时做好遗体保存技术准备”。这些细节传开,京城医学圈子里一片唏嘘,“淮海战役般的抢救”成为口头禅。

议而未决之际,胡耀邦翻看会诊记录,眉头紧锁。据当时在场的一位秘书回忆,胡总书记在批示单上只写下十个遒劲大字:“务必全力救治,请来。”短短一句,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南粤一位47岁的副教授身上。外界不解:广州医学院呼吸内科虽有名气,可北方顶级专家云集,为何非要请他?答案藏在钟家两代人的履历里。
火车一路向北,钟南山在硬座车厢里挤了二十多个小时,身旁推着随手装的三只简易箱:肺功能检测仪、一摞病历、几本英文期刊。同行的年轻助手打趣,“教授,坐飞机快得多。”钟南山摆手,“医疗器械怕颠,也怕气压差,稳妥最重要。”他的谨慎,来自骨子里的职业习惯,更来自父亲钟世藩的耳提面命。

时间拨回到1901年的厦门。孤儿钟世藩9岁就漂到上海当长工,几乎是踩在社会最底层的泥泞里往上爬。叔父钟广文在江南卖中药,见侄子聪明,咬牙把他送进小学。后面那段逆袭曲线大家耳熟能详:协和医学院、纽约州立大学、医学博士。更值得玩味的,是他1930年代毅然回国,宁做战火中的儿科医生,也不做海外的“包租客”。不少同僚评价,“这人骨头硬,心也热”。
说来有意思,钟世藩回国第二年就遭遇“南京大溃退”,跟着政府机关一路跌跌撞撞撤到贵阳。正是那时,他给新生儿子取名“钟南山”——医院位于钟山之南,寄望孩子挺拔如山。谁料,山还未成型,烽火先熏黑了童年。小钟南山常跟着父亲扎在临时难民诊所,一旁看护士煮纱布、烤注射针头。掐指算来,他八岁那年就能帮忙递器械、记体温。
抗战一结束,钟家举家南下广州。岭南大学附小、华南师大附中、高考进北京医学院——路径听着顺,可过程并不顺滑。那位同学口中的“钟运动员”在大学里忙着练跨栏、跳高,非典型学霸一个。1959年首届全运会北京集训,他跑出54秒2,刷新国内400米栏最好成绩,却因伤无缘正赛。钟南山后来回忆,“那段时间,大概父亲也替我着急,一直没说破。”

直到1970年代初,他在广州被分配到呼吸内科。工业快速扩张,尘肺、慢阻肺患者陡增,病房里咳嗽声此起彼伏。钟南山整宿整宿蹲在床边,记录潮气量、残气量,一堆糨糊味儿的笔记摞起来半臂高。那会儿国内呼吸生理数据缺口大,他跟同事“土法上马”实验:把自行车打气筒改成呼吸泵,用奶瓶橡皮塞做阀门,还真弄出第一批参考值。不得不说,在条件拮据的年代,土办法就是硬通货。
1979年,他拿到苏中友好奖学金,去英国爱丁堡皇家医院进修。导师富兰林对这位亚洲学生颇为惊讶:别人交一篇论文算及格,他三年丢出十三份科研成果,还坚持周末查房。英国人看重敬业,连续两个圣诞节,富兰林都邀请他到家里过节,并开出留下来的高薪合同。钟南山婉拒,“祖国送我来,我要带着技术回去。”这一句跟父亲四十年前的决定何其相似。

回国不久,钟南山凭肺功能测试的创新方法,在国内呼吸医学界占下一席。可当中央下令“请钟南山”时,他的行政级别只是副教授。外行人觉得破格,行内人却心知肚明:那几年里,广东呼吸科收治过一系列疑难病例,抢救成功率高到惊人。不少顶尖医院的进修医生回去后只说一句,“南山那套理念救命。”
再说叶帅病房。会诊首日,钟南山提了三个要求:第一,停用已产生耐药风险的广谱抗生素;第二,立即进行波动性肺功能监测,动态调整机械通气参数;第三,改换气管插管角度,减小创伤并便于吸痰。有人担心风险,他回一句,“搏一把,才有生路。”这语气颇像前线指挥。
连续四十八小时,医务组分三班轮流操作,而钟南山几乎没离开ICU。他一边查阅数据,一边把气体交换曲线画在床头,随手几笔,又快又准。72小时后,叶帅血氧上升到85%,昏迷程度减轻,呼吸机压力逐步下调。病房外,几名工作人员长出一口气,有人悄声说,“人民大会堂的布置要不要撤?”另一人摆手,“先等等。”

第六天凌晨,叶帅睁开眼,先是看天花板,随后做了个缓慢的手势——想喝水。护士拿棉签蘸水,他微微颔首。这细微动作被记录下来,作为意识恢复的关键证据。临床例会上,胡耀邦握着钟南山的手,“你们干得漂亮,确实是奇迹。”语气很平和,却足够庄重。那张照片后来没有公开,但参与会诊的几位医护都记得总书记的神情,“像长辈在夸孩子”。
叶帅的身体到底经不起岁月磨损,两年后还是在北京安详辞世。不过,1984那场“生死拉锯”把我国危重症呼吸治疗整体水平往前推了一大截。随后的制度改革,把叶帅病房实践转化为《急性呼吸衰竭救治规范》,不夸张地说,全国ICU沿用至今的多项流程,都能找到当年钟南山在床头写下的草稿。

有人问钟南山,父亲那辈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?他想了想,“是对病人的诚意。”换句话说,医生与患者之间既是技术关系,也是信任关系。没有后者,前者再先进也可能无效。这话听上去朴素,却是两代钟家人在动荡年代里摸索出的经验。
历史细节常被遗忘,技术革新容易被标签化,唯有人的选择与勇气真正留下痕迹。1984年那趟南北奔波、那几张批示条、那一屋子呼吸机噪音,全都属于一个国家医卫体系成长的节点。至今回看,仍让人感到踏实——关键时刻,总有人挺身而出,这就是“南山精神”的底色。
专业实盘配资,上海股票配资一览表,百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手机上买股票在与两名当地男子交涉后开始了骑马活动
- 下一篇:没有了